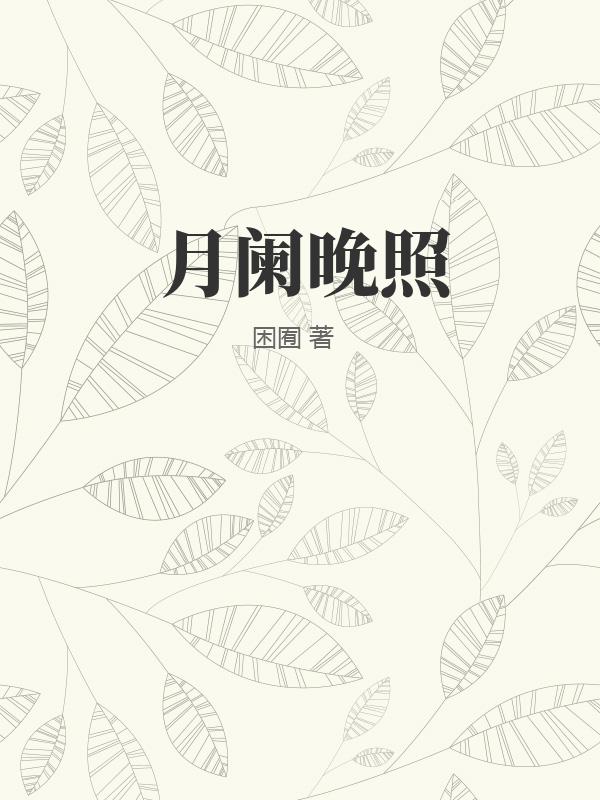与父母说开后,只有扶苏一个人在闷闷不乐,他明白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宿命,可他想不明白那个人为什么是扶光。
若他有一副健壮的身体,他有过人的天赋,那他是不是可以代替扶光。
“苏哥儿,开心点嘛,马上就要到南苏了,莫要让外祖父外祖母以为你见他们很不开心。”扶光揉了揉扶苏的脸,让苦瓜脸扯出一抹笑容。
扶苏扯出一抹比哭还难看的笑,怏怏的说:“光姐儿可满意了?”
“怎么比常喜笑得还难看。”扶光看了一会十分中肯说道。
常喜是扶光养的小宠物,五官总是皱在一起,张不来,笑起来很吓人,之所以叫常喜,是因为常喜总是经常笑,扶苏偶尔看见常喜,但每次都被吓到。
一想到常喜的脸,扶苏脸瞬间白了青,青了黑,好不精彩,冷哼一声就闭上眼睛假寐。
汽车在路上行驶,纵使开得很慢,但坑洼泥泞过多,还是震得车上的人有些难受。
“父亲,可否停一会,我被震得有些难受想吐,头也昏得很。”扶苏在后座有气无力说道,脸色也发白了。
闻言姬康平看着边上停了下来,转头看向扶苏,语气里满满都是嫌弃:“堂堂一男子汉竟比不上女儿郎,你瞧瞧你姐姐,再看看你阿敏姨,就连你母亲都未曾难受。”
扶苏被说得羞红脸,还是忍不住反驳:“这也不能怪我,我是第一次坐车回南苏的,况且,况且我身体原本就不好,坐了好几天的车,哪能好好休息,身体吃不消不是很正常的事吗?况且出发前两天我都没休息好,我如今没旧病复发都是万幸。”
扶苏越说学理直气壮。
那天客厅谈话后,第二天姬康平就去公司交代副总经理一些事,然后便拉着他们出去开介绍信,买各种东西,又收拾行李,第三天天还不亮就出发,他这羸弱的身体怎么吃得消啊。
“你小子现在还敢还嘴了?”姬康平作势就要打扶苏,扶苏害怕地缩在扶光背后,回答道:“儿子不敢。”
“你还不敢,我看你敢得很,我都开了三天的车了,我都没说我身体吃不消。”
“那可不一样,父亲身强体壮的,又自幼学习武术,身体那是叫一个好。”扶苏撇了撇嘴说道。
“那是,也不看看你父亲是谁。”姬康平被扶苏这么一夸,整个人也有些骄傲起来:“我可是姬家最能打的那个。”
“谁说不是呢,被二位伯爹追着打长大的。”扶苏嘟囔了几句还是被姬康平听见了。
“你小子在说什么?”
扶苏连连摆手,直说夸他厉害,是姬家最能打之人,又说自己闭眼休息一会。
一行人休憩了半个小时,又重新出发,这次直到南苏宋家,扶苏也没喊头晕。
姬康平将车子停好,提上早就准备好的东西带着家人扣响宋家大门。
“是谁?今日我家先生身体不适不宜见客!”许久里面就传来一道浑浊苍老的声音。
“元娘,是我,蕊姐儿。”宋卉蕊听出了里面老人的声音,立马开口说道。
下一秒大门被打开,元娘头发已经发白,眼神也不利索了,盯着宋卉蕊看了许久才悠悠说道:“是了,是蕊姐儿。”
“蕊姐儿,姑爷,光姐儿苏哥儿,阿敏你们回来了!快快进屋,外头寒冷。”
元娘又将其他人看了个遍将人邀进来。
“元娘,父亲身体如何,可去医院看了医生?”宋卉蕊惦记着父亲身体健康,等到元娘落了锁才开口问。
“瞧了,医生说是老毛病了。”元娘一边领着大家往客厅走一边说道:“昨日夫人才写了信叫我今日寄给蕊姐儿,没想到你们今日就回来了,也好也好。”
元娘身体大不如从前,步履蹒跚,宋卉蕊生怕她走路摔着,便扶着她走。
元娘笑了笑没在说什么,从大门到客厅不过百米距离就已经气喘吁吁,直呼自己老了不中用了。
“你们先坐着吧,我去给你们倒杯茶。”
“元娘不必如此麻烦,叫阿敏去就行。”
元娘也觉得自己的身体现在疲劳极了也就同意宋卉蕊的说法,找了椅子坐下才说:“敏丫头啊,这家你也熟悉,东西大概就在原来的地方,若是瞧不见,得麻烦你找找了。”
“说什么麻烦不麻烦的。”阿敏将手中的东西放下后就起身去了厨房。
宋卉蕊担心父亲身体,没等阿敏倒茶水来,就带着丈夫与儿女去看父亲了。
还未走进老爷子的房间,众人就闻到了重重的药味。
元娘敲了敲门便推门而入:“老爷夫人,你们看是谁回来了?”
坐在床沿上看账本的老妇人转头一看,瞬间眼里泪光闪闪:“我儿回来了!”
“是蕊姐儿啊!来,坐坐坐。”躺在床上的老爷子听到声音也慢慢翻过身来,见到宋卉蕊眼里也隐隐闪过泪光,枯瘦如柴的手拍了拍妻子旁边的位置。
“父亲,母亲,”宋卉蕊快步走到两位老人面前:“经年一别,许久未见,父亲母亲身体可还安康。”
宋卉蕊说着说着眼泪便流了出来,她没有想到,不过三秋未见,父母已然苍老许多,还记得上次见面,父母鬓角还未有银发,如今已是满头白雪。
“安康安康,”宋母不想女儿担忧,细细替女儿擦拭泪珠,又想起房中药味浓郁,连忙补说道:“只不过近日来,你父亲他……偶感风寒,倒也没什么大碍,只是你怎的忽然回来,还拖家带口的,可是女婿生意上有难处,需要我们的帮忙?”
宋卉蕊听到宋母的话,泪水更是汹涌,虽然元娘未明说,她亦是猜到父亲的情况,怕是不好了。可纵使如此,母亲依旧担忧她们。
姬康平等人见到宋母提到自己纷纷鞠躬问好:“岳丈(外祖父),岳母(外祖母)”
“小婿生意上并无难处,只是蕊蕊思念家人,故而回来瞧瞧。”姬康平微微低头说道。
“好好好,是否多住几日?”宋母用帕子拭去眼角的泪,问道。
姬康平想也没想说道:“今年,我们在南苏过年。”
“好好好,元娘啊,你明日叫黎生多准备些年货,我们一家好好过个年。”
听闻,宋母眼中的高兴快要溢出来了:“家中已经许久未有这么热闹过了,甚好甚好。”
元娘笑着应了,就走出去了。
“都站着作甚,你们自己快快寻个凳子椅子坐下。”看到姬康平她们还站在,便打趣说道:“莫不是要让我这老婆子亲自给你们端过来?”
姬康平等人连连摆手说不敢,然后拿了几条凳子坐在宋父傍边。
“光姐儿苏哥儿都长这么大了,今年十八了吧?模样可真真是俊得很,也不知道以后我们光姐儿便宜了哪家小子,苏哥儿你可曾有心仪的姑娘,跟外祖母说说。”
“多谢外祖母夸赞,只不过我和苏哥儿(光姐儿)还小,暂时不考虑这些。”扶光与扶苏对视一眼,然后异口同声说道。
宋母笑呵呵,不以为然的摆摆手:“遇上对眼的,自然就会考虑了,当年你们母亲也是这般说,结果还没两月就遇上你们父亲了,当时她也才像你们这样大,这一转眼你们都这么大了,果真是岁月不饶人啊。”
“你们怕是不知道,当时你们父亲差点被你们外祖父给打死。”
被长辈这样说,姬康平多少也有点不好意思:“岳母跟孩子们说这个作甚。”
“其实我们来南苏是有件事要告诉二老的。”
“何事?”一直沉默寡言的宋父忽然开口。
姬康平轻咳两声,看妻儿都没有要说的打算,便悠悠开口。
“光姐儿要下乡插队去了。”
宋家二老并不知晓扶光工作特殊,而扶光也没跟二老说过,故而她们商量说去乡下插队。
一来是不好解释扶光的工作,二来是不想二老为此担忧。
“光姐儿,你为何要去插队,莫不是你父亲偏心眼,故意没给你安排工作,把你赶到乡下去?若真是如此你莫怕,咱宋家也能给你安排个工作,不说有多好,但至少比干农活轻松。”
宋家二老一生就宋卉蕊一个女儿,自幼将她千娇百宠着长大,而扶光又酷似宋卉蕊,宋母更是爱屋及乌。
宋母说完越觉得自己的猜想是正确的,狠狠剜了姬康平一眼。
姬康平只觉得无辜,对于女儿他也是疼惜得不行,若女儿是普通人,他定然舍不得女儿去乡下吃苦。
“外祖母误会了,是外孙女自个儿要下乡的,与父亲无关。”
宋母细细盯着扶光,见她没有说谎的迹象,便摆摆手:“光姐儿你糊涂啊!那乡下是你该去的地方吗?你去了乡下可要风吹日晒天天做农活,罢了罢了,你要去的是何方,何时出发?”
见外孙女都被自己说得委屈都快要哭了,宋母也不舍得多说什么。
“外祖母,外孙女正月十六便要出发,去的地方在南方,一个叫裴畲的地方。”
见宋母不再说,她眼里的泪光瞬间收了回去,温温顺顺的回答宋母的问题。
“你要去何方?光姐儿你再说一遍!”
扶光以为外祖父没听清,又将地名重复了一遍:“外祖父,外孙女要去的地方是裴畲。”
“裴畲啊~”宋父小声呢喃了一句,目光渐渐涣散,思绪也飘远。
房间里的人都没有打扰,须臾目光才重新聚集。
“罢了罢了,华娘,你去书房帮我把那个木盒子拿过来。”
看宋母出去后宋父就让扶光坐在刚才宋母坐过的地方:“光姐儿,外祖父有一事相求。”
“外祖父但说无妨。”
宋父叹了一口气,目光似乎在回忆:“在裴畲有外祖父的一位故人,他是我年少时至交好友,后来因为一些矛盾,他去了裴畲,从此了无音讯,至今已有四十余载,你去了裴畲,能否替外祖父去瞧瞧他如今过得好不好,顺便告诉他我与你外祖母都十分想念他,这些年心里也一直记挂着他,我也知晓这事很难,你尽力而为便好,不用特意去寻他,若是你能见到他说明我们缘分未尽,若是不能也是天命。”
许是大寿将至,短短几句话,宋父分了好几次才说完,话也有些颠三倒四的。
具体的扶光听懂了,想着对她来说不是难事便应下了:“扶光定当尽力为之,外祖父可否将故人之名告诉扶光,以便扶光找人。”
“他啊,他叫陆白,字怀之,我与你外祖母一般都叫他黑狗,春明人士。”
宋父在说到黑狗时不由得轻笑一声。
“华娘,你快把玉佩拿给光姐儿。”
看到宋母进来,宋父立马示意宋母把盒子交给扶光。
说到故人,宋父的精神好了些:“玉佩原本是一块的,后来一分为四,我与你外祖母以及你那位陆爷爷一人一小块,还有一块在你陆爷爷的爱人手上,他爱人病逝后一直是他在保管,你只要带着这两块玉佩去,他保准能认出你,就是不晓得他还认不认我……”
宋父的声音越说越小声,最后归于平静,宋母抽了抽鼻子,细心地给宋父掖好被子。
“咱们去客厅聊天吧!”宋母说道。
宋父现在睡得沉,可宋母依旧不愿意打扰宋父,便带人去了客厅。
“外祖母,可否将你们的故事讲与我们听。”
一到客厅,扶苏便迫不及待的坐到宋母身边小声央求:“外祖母:求求你。”
扶苏与扶光是双生子,与扶光容貌无异,自然也颇得宋母怜爱,宋母点了点扶苏额头,笑骂道:“就你八卦,堂堂男儿怎可如此八卦。”
宋母还是说了。
“我们四人曾经是最要好的,你外祖父与怀之是好兄弟,我与怀之爱人秋宜亦是闺中密友,当年秋宜在战火中产子,在转移时血流过多而亡,怀之失去了心爱之人,又不肯信我们的解释,最后带着幼子离我们而去,他总是说若是我们再快些,秋宜便不会死。
宋母又说了许多许多,直到元娘来叫她们吃饭才结束了这个话题。